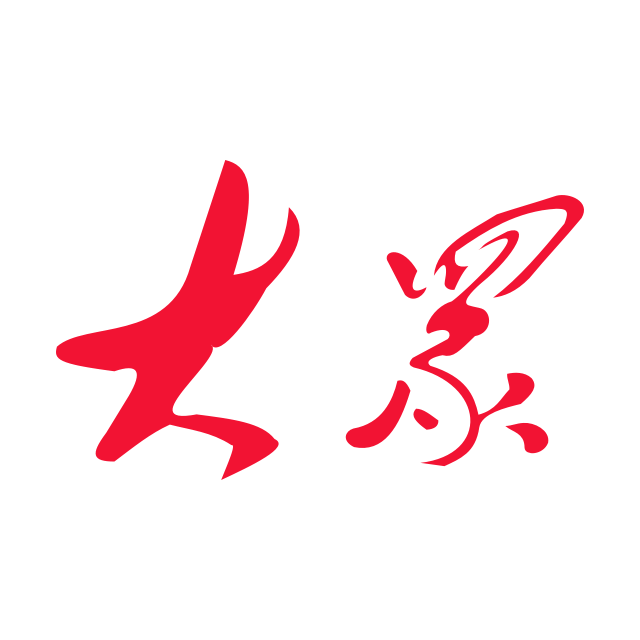病痛与疗救——王涛小说《〈康复时代〉四部曲》荒诞美学浅论
博览 | 2025-04-07 09:17:09原创
来源:大众新闻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疾病的隐喻》中指出,疾病常被赋予道德、政治与美学意义,在文学中往往被设置为多重象征体系。比如,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霍乱”被视为对底层人“不洁生活”的惩罚;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将“肺痨”与国民性愚昧捆绑,疾病成为社会病态的缩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在为《康复时代》所写的推荐语说:“从《忧郁时刻》到《疾病传说》,作者将疾病编码为时代隐喻,在虚构的病症肌理中,我们触摸到整个民族隐而未宣的集体症候。”所以,解读作家王涛的《康复时代》,就需要在文学史的卷轴上,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比照“四部曲”所折射出的时代特征,确认“疾病”这一能指符码的所指意义。

虽然苏珊·桑塔格在替作为隐喻的“疾病”祛魅,但作为小说叙事聚集点的“疾病”视角,绝不会只是一个叙事的能指符号,也不只是叙述“疾病”的生理或肉身痛感,关注更多还是心理、精神上的焦虑或不安,因此,“疾病”不止于作为个体存在的镜像,而且还是一面社会批判的多棱镜。《疾病传说》中“饕餮综合症”表现出来的无尽的个人“贪欲”,《诊断报告》中“强迫症”中来自内心深处的“控制欲”,两者侧重于个体的存在;而《忧郁时刻》的“忧郁症”和《中毒反应》的“疯狂”病症则极具社会批判性。
小说四部曲所叙述的各种“疾病”均撕裂了人与世界的理性关系,如,《疾病传说》中“柳兰芽的风月”,柳兰芽与童小星是一对恋人,正常的男女恋爱当然不会排除情感上的纠葛,但因柳兰芽的个人出身,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心中不断成长的那条“饕餮之虫”,先是刺破了柳兰芽做个贞节女的愿望,而后这对有情男女也终成陌路之人。“石未来的旅程”中功成名就的吴茁壮始终未能释怀少年时代对余离离的爱而不得,于是,他以精心编织的温柔陷阱诱使余离离与石未来离婚。当余离离挣脱婚姻枷锁后,吴茁壮却骤然抽身离去,最后余离离也只能在支离破碎的情感废墟中沉沦。小说的叙述虽说立足于现实,紧贴生活日常,但在故事情节安排上,小说家却有意将人物的成长史或情感过程处理得既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也违背了道德伦理,加缪将这一病态的社会现实称其为“荒诞”。
小说借“疾病叙事”剖开我们生存境遇中令人震颤的“荒诞性”,《康复时代》诸多被疾病撕裂的人物,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荒诞世界的疾病图谱。如《诊断报告》中的革命者李戈耀,在革命初期,她以违反革命纪律的方式进行“革命”,革命胜利后,又因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再如,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莫博赏,他自己是研究强迫症的医生,在给心理病人治病的同时,发现自己也是一位“强迫症”患者,为了彻底搞清楚强迫症疾病的病因,他似乎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对他发号施令,莫博赏决心要把那个控制他行为的“影子”抓住。他费尽了各种周折,终于把那个越来越清晰且渐渐长大的影子抓到了。影子告诉他,它是他的儿子,为了自身的长大,它不但要控制他的行为,而且要最终吃掉他的性命。莫博赏大惊失色,决定把它彻底杀掉,以阻断它对他的毁灭。于是,莫博赏使出浑身的力量,把围拢着它脖颈的两手急快地收紧。莫博赏从频临崩溃的迷幻状态中醒来后,发现把自己的命根扯断了。其他病患人物还有李百家、姜无疾、李达理等,皆可如是观。
这些试图与世界建立理性关系的人,最后都走向了非理性,这种荒诞的本质是悖谬性。也是悲剧得以生成的根本原因,所以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鲁迅小说《药》的荒诞性就建立在“人血馒头”既是治病的药,又是杀人的刀的悖论上。这种悲剧性的荒诞,不仅体现在个体命运的断裂中,还反映在社会整体的失序与混乱里。如《忧郁时刻》,李蒙克的纵火案被嫁接成周岫娟的“自首”,张效梁的死亡被改写为自杀殉情,美国律师的遗产馈赠成为植物人父亲的伦理黑洞。这种“真相的不存在”恰好印证了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所言:“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与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每个角色都在编织自洽的生存逻辑,但这些逻辑最终都在他者叙事中分崩离析。派出所对纵火犯的两次“无罪释放”,警察以制造谣言为名将李蒙克送入精神病院,市长用电视演讲消解洪水预警,这些场景构成福柯式“规训社会”的加缪变体。制度不再承担维系秩序的功能,反而成为荒诞的生产商。小说里的爱情关系都是以拯救开始,以互害结束。夏海丽将婚恋异化为财产分割方案,周岫娟用纵火完成对丈夫的终极占有,不论男人还是女人,皆想在情欲中寻找存在支点,结局却制造出更血腥的荒诞现场。
如果将荒诞世界的“疾病”这一集体症候进行切片化验,那么悖论性是其最主要的病理结论。由此可以看到,“饕餮综合症”“强迫症”是一种个体的病痛,而“忧郁症”除了个体“中毒”之外,更多的是其病症的社会“毒性”。面对荒诞的人生和社会,海德格尔提出要在“沉沦”的生活实现中知觉到“畏”,摆脱“非本真”的人生,进而达到“本真”状态。如托马斯•曼的《魔山》,疾病成为汉斯超越平庸的动力,在“向死而生”的生命体验中直面存在的荒诞性,疗养院对汉斯来说不但是“魔山”,还是炼狱;加缪同样在他的小说《鼠疫》中把奥兰城居民抛入一种集体流放的状态,人类在荒诞世界中被剥夺了意义归属,面对鼠疫,里厄医生选择以“诚实的无知”投入抗争,医生“承认荒诞的存在,但拒绝屈服于荒诞。”
与萨特的以文学“介入”社会的理论不同,针对世界的荒诞,加缪选择了“反抗”,即对无意义世界的抗争。作家在《康复时代》中,暴露“病痛”之后,便是“疗救”。李蒙克一直在追踪妻子、几次探访乌龙镇,这种不断“迷失”之后的不断“寻找”,使他在每次接近真相后,都会陷入更大的荒诞结局,但却具有了西西弗斯反复推石上山,不屈于命运折磨的抗争意味;莫医生四次回到乌龙镇,表面是对不同人物死亡原因的调查,实际却是他逐渐认识“强迫症”的过程,对“强迫症”了解的越清晰,他对世界荒诞的反抗亦就越强烈,他遭到“疾病”的反噬也就越严重,所以,当他处在加缪所言“觉醒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却进入了反抗即是对荒诞献祭的困境。“四部曲”对世界“荒诞性”的反抗停留在两个层次上,莫医生、李蒙克,包括李二女,都是经由物理肉身“死亡”的反抗;李线长虽说与之不同,他的抗争也只是在宗教或哲学的“死亡”层面上。加缪认为,反抗不在个人而在集体,在《鼠疫》中他没有坠入对“荒诞”的绝望渲染中,而是通过反抗者的群像(里厄、塔鲁、格朗等)传递出一种“悲观的英雄主义”。即便荒诞是人类永恒的宿命,加缪才说:真正的胜利在于记住苦难,记住抗争,记住在黑暗中彼此紧握的手。
反抗就要有所行动,里厄来往于奥兰城病患者之间,李四平为消灭“毒蘑菇”几乎扎根莫邪山中,凭着坚强的毅力实现了对家庭荒诞命运的抗争。小说《康复时代》四部曲的“疗救”指向十分鲜明,借由“疾病叙事”作家构建“荒诞”乌龙镇这个文学疆域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把“手术刀”递到读者手中,先去解剖自我,然后再剖析社会,力图在“病痛”之后开出一张“疗救”人性与社会的诊断书。(张秀功)
责任编辑:吕晗